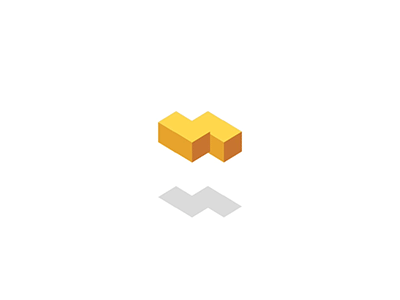基督教四次传入中国,历经中国的唐朝、元朝、明朝、清朝及民国,跨越历史长河1300年之久,从太平盛世唐朝到风雨飘摇的晚清。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曾出现“法流十道、寺满京城”盛况,却在逼迫中烟消云散。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开启了基督新教在华宣教之门。此时正是中国社会历经变革、动荡的年代,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非基运动接二连三出现,全民陷入疯狂的“运动”。
基督新教一开始就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来到中国,自然就会受到中国人的抵制、排斥。基督信仰如何在中华大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传教士寻找的宣教策略,各差会根据各自的神学立场及传教士处境,各种传教方式百花齐放。
教会史学家一般以传教士戴德生与李提摩太为代表,分为两条传教的路线,著名的史学家赖德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注意到这两位传教士之间的不同,他说:“戴德生和李提摩太是任务不同而且概念时有冲突的传教士的杰出代言人。”本文从戴德生和李提摩太信仰经历入手,探讨他们信仰经历与宣教路线关系及对温州教会的影响及反思。
一、戴德生的“平民或直接宣教”
戴德生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班士尼镇,父母都是循道会的信徒。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向往中国宣教。十三岁时不满学校的教育,辞学回家受教,并在父亲的药房帮忙。十五岁考入班士尼镇一家银行,从事初级文员。在银行工作期间受同事的影响,对信仰产生了反思。十七岁时生命中遇见了耶稣,开始投入到教会中服侍,带领许多年轻人归信耶稣。父亲经常给戴德生讲马礼逊、郭实猎等在华传教士的故事,神透过这些传教士的故事呼召他前往中国宣教。戴德生得知在中国医疗传道很重要,于是他集中精力开始学习医学、中文,另外在体能方面锻炼自己,预备迎接前面艰难的日子。为了适应在陌生的环境传教,戴德生还在信心上操练自己,学习完全依赖神的生活。1852年戴德生接受中国传道会安排来到伦敦医院学习。1853年《海外布道杂志》报道了有关太平天国的事迹,这些报道在戴德生心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放弃医院的学习,立刻动身到中国。此时戴德生没有圣职、没有医生的资格,只带着信心前往中国宣教。1854年3月1日抵达上海,开始六年中国宣教。六年后因个人健康原因返回英国。在逗留伦敦期间神给他一个异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它将会是一个海外布道团体,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对宣教、植堂和教会培训有很负担的男女信徒组织而成。他们需要借着祈祷,单单信靠神的引导和供给,进入中国内地,向十一省未得之民传道。由于戴德生不确定这个组织策略和可行性,造成他心理上有很多顾虑,心神不宁,最终病倒了。好友邀请他去伯莱墩休假,在沙滩上漫步时,灵里极其痛苦;戴德生后来回忆说:“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让我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献上自己,为他所用。我把一切困难和后果交托他,服从他,跟随他——由他引导,由他看顾,由他带领。平安立刻就涌进我烦恼的心里。”他从海边回到城里,立刻去银行用“中国内地会”名义开了一个户口,存入十镑,虽然数目不多,但戴德生说:“它是十镑另加神所有的应许。”这天(1865年6月25日)标志着中国内地会成立,这完全是出于戴德生个人信心的行动,故此“中国内地会”这个名字其实就代表着戴德生的传教路线。
笔者根据戴德生信仰上的经历,总结戴德生及内地会宣教路线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信心的路线:戴德生被神呼召来中国宣教时,他就想到耶稣差遗门徒出去没有带任何的物资,完全仰望上帝在工场上的供应。虽然那位牧师认为戴德生年轻太单纯了,只要他长大一点,就会变得聪明一些,但是戴德生许多年之后回忆说:“我现在已经长大多了,但并没有变得聪明一点。我只是越来越相信如果我们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对初期使徒所作的保证,那么这些提示和保证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时代。”为了预备自己在中国信心宣教,他在伦敦受装备期间就学习信心的操练,完全仰望神的供应。另外他给内地会定了两条规定:第一、内地会不会进行募捐,也不设收捐站;捐献者的名单亦不公布。第二、内地会的传教士并无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应;所有收入大家分用,不能向外借贷。
2. 平民的路线:戴德生第一次来中国就以“平民”的身份来,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没有取得医生资格。他设立的内地会延续着这种“平民”或“全民皆传教士”的风格,其它差会选立的传教士都要先按立为牧师,最好是大学毕业。然而他选择的传教士标准聪明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论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属灵质素,对神的信实绝不疑惑,甚至他差派单身女传教士到中国宣教。在他所定的内地会的会规里有这样一条:“它的传教士并非来自一个宗派,而是从许多教会来的,只要他们签署一份简单的信仰宣言即可。”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带领第一批内地会的传教士来中国,这十六名年轻传教士有铁匠倪义来、木匠卫养生、石匠童跟福、木匠蔡文才、铁匠或机器修理师路惠理、女传道麦克莲、两位大学毕业的姑娘、秘书白安美、福珍妮、女教师包玛莉、苏珊、史洪道等。这份名单里所记录的传教士给笔者看到内地会推动了“信徒皆传教士”的理念,每一位“平民”都是上帝所拣选的传教士。另外,戴德生及内地会在中国宣教对象:中下层百姓---平民。教会史学家称戴德生的传教路线为平民路线,主要是指他们向中国的百姓传福音。
戴德生为了深入中国内地宣教,为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他自己穿上中国服装。并且规定内地会所有传教士均穿着中国服装,在中国式的房子内崇拜,而非像宁波的西式教堂。这种“平民”宣教方式让中国人与基督教之间减少“洋”味,是一种完全平民化的宣教路线。
3. 福音的路线:史学家也称直接路线,就是直接传讲福音的核心内容,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拯救罪人的福音。在《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录戴德生第一次来中国不久外出向一位老人传福音的故事,他向这位老人传讲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引用大量的神迹奇事及耶稣的复活,说明耶稣是神,与中国人所理解的圣人不同。当他看到中国活在迷信、黑暗的权势之下,并被贪婪充满,戴德生认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拯救中国人,给中华大地带来光明。对于戴德生而言医疗、教育传教是直接传教附属品,最主要的就是直接宣讲福音,只有福音才能改变中国人的心。
笔者认为戴德生采取直接宣教路线另一个原因是与他的末世论有关,这个世界是暂时的,眼看见的一切都要过去,基督徒所盼望的是耶稣复临时所带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进入耶稣为重生的人所预备的新世界,谁能重生呢?只有福音才能重生人。故此,戴德生看到中国每天有三万三千人没有听到福音,在毫无盼望的情况下死去,他内心焦急万分,因此他设立中国内地会的目的就是尽快把福音传向全中国,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在内地会的会规里有一条如此说:“要福音传遍中国……目的并非增加内地会的人数,而是尽快使福音传遍整个中华。”
二、李提摩太的“精英与间接路线”
李提摩太于1845年出生在卡马登郡一个名叫弗迪布兰宁的村子,父母是虔诚的浸礼会信徒,父亲曾在两处浸礼会教堂担任秘书兼执事。李提摩太就读公理会教会附属学校,直到十四岁时,父亲希望他回家务农,李提摩太却有强烈的读书欲望。他请求父亲再支持他一年,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不再伸手向家里要钱。15岁时他实现了诺言,他一边读书一边在矿山小学当教师,他用自己钱继续求学。1865年,他考入哈弗福特韦脱神学院。
1866年戴德生带领第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这个事件引起了李提摩太的注意。1868年李提摩太再一次听到有关内地会传教事迹,他如此描述说:“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我,在哈弗福特韦脱神学院的求学临近结束时,我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由于他是浸礼会的信徒,内地会建议他向浸礼会对外传教提出申请。他听从了建议,向浸礼会提出了申请,并希望被派往中国北方。1869年春天,浸礼会批准了他前往中国宣教。1870年2月抵达上海开始了他人生第一个阶段的宣教生涯。李提摩太采取传统传教方式:街头布道、发福音小册子、旅行布道等,他发现这些布道没有什么成效,因而感到十分沮丧。那些商人、绅士根本不会听外国人布道,参与聆听的人大多数来自农村、偶尔跟过的流浪者。从那以后,李提摩太开始寻找新的宣教的路线。
他的新宣教路线与浸礼会的路线不同,期间与其他传教士产生了冲突,他决定离开浸礼会加入广学会,开始他人生第二个阶段宣教生活。1916年退休回英国时,他已经获得美国神学博士、文学博士、法学博士及大清朝皇帝赐予的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三代的荣典等荣誉。
笔者根据李提摩太信仰的经历,总结李提摩太及广学会宣教路线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精英的路线:按李提摩太自已的说法“寻找上等人”。他说:“我意识到,他们形成的土壤,最适合于我们播种福音的种子。”苏慧廉如此评价这种传教路线:“这是一种传教士们应该优先采纳的方法,尤其对于那些正直的、不带有敌意和优越感,满怀着纯粹的友好态度、随时准备以一种愉快的心情接纳一切美好事物的传教士而言。……要是我们的教会能够采纳他从主那里领悟到的这一方法,向其他宗教的上层派出最具魅力的代表人物,以一种宽容和怜悯之心来传播主的旨意以拯救这个世界该有多好!为了寻找上等人,他寻找佛教著名的法师、伊斯兰教阿訇毛拉及教授、道士与他们对话、交流,研究儒、佛、道经典著作。李提摩太从爱德华·欧文著名的传教布道中认识到最好的传教方法是去拜访思想和文化上的领军人物。他结交各地儒家学者及官员,比如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甚至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变法,差一点还作了光绪帝的外国顾问。
李提摩太认为其它宗教及社会领袖是“上等人”,是接受福音的好土。故此,他认为其它宗教里也有上帝的“启示”,如佛教《华莲经》、《起信论》及《西游记》是被景教影响或就是景教的著作。因此他大胆采用这些宗教小册子直接改写成福音小册子。这种做法导致他与戴德生及浸礼会其他传教士的冲突、分歧,最后双方分开。
2. 间接的路线:戴德生以福音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迷信,李提摩太以教育、科技等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迷信。他说:“我认识到,驱除这种迷信的最好途经就是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我坚持认为,应当付出跟从事宗教事务同样多的努力去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上帝制定的法律。”就是这种精神引导着李提摩太对教育、医学、科学、物理、社会改革、政治改良等事工上,不断的向各地官员、慈禧太后及皇帝献计献策,改良中国的教育、政治等环境。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创办一所西式高等学府,他为了这所学府离开浸礼会,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最终用庚子教案赔款创建了山西大学。
3. 文字的路线:李提摩太在华宣教一生其实也是文字宣教的一生。他来到中国不久,就认识到早期传教士写的福音小册子不适合中国人阅读,容易产生矛盾,故此他大量的阅读中国其它宗教及儒家的经典著作,采用这些典籍中的宗教思想和词汇,编写《教义问答》,还翻译了《拯救之道》等著品。离开浸礼会后先加入《时报》社,当中文报纸的主笔,后加入广学会担任全职文字事工的传教士。他人生的下半场一直服侍广学会,从事文字宣教的工作。他通过写书及翻译西方经典著作的出版,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官员,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教育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两种宣教路线对温州教会的影响及反思
很明显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在宣教的路线存在差异,姚西伊博士精辟总结说,李提摩太试图通过他的传教工作来促进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或者说要在地上实现上帝的国度;而戴德生则始终以福音为中心。……前者要以介绍西方近代文明和改革社会,或者说以福音的果子引导中国归向基督;而后者则要在基督复临之前,尽可能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前者瞄准中国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以他们为传教对象;后者则致力于向中国内地的大众传播福音。前者卷入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政治的改革中,后者则从不容许福音的任务被任何其他事工上所干扰。前者注重与其他宗教发展友好关系,后者则从不含量糊地坚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和其他宗教传统的谬误。另有学者如此总结,戴德生是要求更多的人来带领一百万中国人信耶稣,李提摩太却寻找藉着一个人带领一百万人信耶稣的方法。
追溯温州教会历史,新教来温第一个传教士曹雅直属于内地会,是内地会早期传教士之一。1876年11月抵达温州,宣教路线完全依照戴德生的路线,在温州传道十一年,于1889年病逝法国。1883年偕我公会传教士苏慧廉来到了温州,开始24年在温州的宣教生涯,他旅行布道,创办学校、医院、翻译温州话圣经等。1907年转入山西大学,正式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1920年,苏慧廉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对比温州两位传教士的两种宣教路线,前者受戴德生影响,后者受李提摩太影响。但他们在温州期间相互合作,相互包容,拓展福音,如今温州被外界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与他们当年宣教是有直接的关系。
文革是温州教会另一个起点,或者说是戴德生“平民”、“福音”、“信心”路线的大复兴。在教会遭受大逼迫,教牧人员被囚禁,此时平信徒兴起取代了传统圣职人员。这些教会领袖注重个人得救、圣灵的充满、盼望基督复临、盼望新天新地,在艰难的环境中凭信心仰望神的应许。
改革开放后温州教会在宣教路线延续戴德生的宣教路线,有强烈的福音使命感,各地区组成温州福音组,向温州山区及外省差派传教士。另外也随着温州商人、学生外出,福音随着温州基督徒商人、学生带向了全国各地,建立起温州模式的教会及各城市新兴教会。温州本地随着民工潮来临,温州各牧区举办各类的布道会,民工艺术团布道,涌现出各类民工教会。2000年以后温州本土教会年轻传道人意识到文字宣教、基督教教育等事工重要。各地区温州教会出版内部刊物、福音杂志、史记,比如:《麦种》、《惟真》、《中国耶路撒冷--温州教会史》等。个别教会开展全日制幼儿教育及在家初中级以下的教育。
故此,笔者认为戴德生及李提摩太两种宣教路线并不是对立的两种模式,虽然李提摩太的某些神学观点笔者不能认同,但是他对全方位宣教态度及制造宣教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及处境化是当代温州教会必须要反思的部分。不过寻找政治上等人,想影响一个人改变全中国的这种宣教路线在中国是失败的,从景教、也里可温至明清耶稣会,是历来传教士一贯路线,历史给我们看到走上层路线宣教没能生根在中华大地土壤里。正如法国天主教神父沙百里所说的,‘西方有关创建一个基督徒中华帝国的大梦终告结束。这是一场悲剧性和滑稽可笑的梦。悲剧性是西方基督徒们落入了自己那不具有不同程度的荣耀历史的陷阱,认为必须在另一个世界重复这种历史;滑稽可笑的则是,如果人们考虑到他们自己使命的内容,那就是一种不在本世界上存在的王国之希望。’事实给我们看到戴德生的“平民”路线深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在动荡的文革期间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硕果累累。
就目前中国·温州的政治环境而言,温州教会要预备戴德生所具有的那颗‘完全凭信心、信徒皆传教士、宣讲救罪人之福音’的宣教心,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到各各它的宣教路线。才能在这场大风暴中继续不断的扎根、不断的结果。
注解:
1.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in China,387.载于姚西伊,《为真道争辩》(香港:宣道,2008),30。
2. 戴德生向公理会的一位牧师借阅《中国的现在与将来》,牧师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借阅此书呢?”戴德生回答说:“神呼召我把生命献出,到中国传道。”牧师继续问他:“那么你计划怎样到中国去呢?”“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会像初期犹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一样,没有杖,没有袋,没有粮,没有钱,出去时全然倚靠那位应的主。”载于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梁元生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11。
3. 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123。
4. 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124。
5. 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125。
6. 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11–12。
7. 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125。
8. 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125。
9. 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126。
10. 史蒂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126。
11.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 侯林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
12.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33。
13.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33。
14. 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关志远和关志英等译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5。
15. 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65。
16. 李提摩太阅读《起信论》心得:我静静地坐着阅读那本使那位儒生转变佛教徒劳无功的经书,直到夜里一两点钟。最后,我向同室的希尔大声喊着:“听着,这是一本基督教的经典,尽管所用的术语昌佛教的,但它的思想是基督的。”载于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177。
17. 我也充分利用了当地一些非常通俗的宗教小册子,剔除了其中的偶像崇拜成分,插入了对惟一真神的信仰的内容。载于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76。
18.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104。
19. 姚西伊,《为真道争辩》,31。
20. 根据《中国近代大学创立和发展的路径》(第269页)记录,苏慧廉于1907年7月抵达大原,原总教习郭崇礼1906年8月去世,苏慧廉来山西接任。
21. 考察苏慧廉的传教方法,可明显看出李提摩太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自1884年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开始了。1919年李提摩太去世后,苏慧廉着手为他立传。他认为,这个人曾为乱世人心开路。载于,沈迦,《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2013)237–38。
22.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郑德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0。
(本文作者系浙江瓯北一教会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