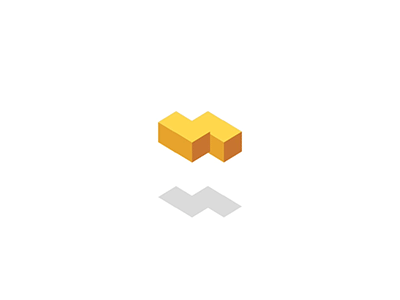一、问题提出
农村金融的供给与需求机制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 这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的维系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农户金融需求方面来看, 叶敬忠指出农户的消费性金融需求强烈。[1] 实际上,消费性金融需求可分为两类, 即仪式性消费金融需求与日常性消费金融需求。农户的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仪式性方面, 即为给儿子完成娶妻的人生任务而在彩礼、建房与办酒席等方面所产生的资金需求。仪式性消费的开支受到当下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影响而不断增长。目前在田村, 即将结婚的女方一般会向男方提出两三万的彩礼和在县城买房的要求。然而, 男方单纯依靠打工或务农是没有能力支付的。因此, 借贷也就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在此情形下, 农户的仪式性消费资金需求满足的途径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从农村金融供给方面来看, 已有麦金农的现代金融机构与落后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理论,[2](P76-90) 张凤对民间金融具有的交易成本低与信贷信息对称等优势的分析,[3] 以及邵传林、徐立新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较高效率的理解。[4] 总体上看, 学术界既有的民间借贷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分析了农户对正规金融部门的需求抑制, 并认为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主要依托于非正规金融, 但这些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制度层面探讨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 缺乏对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社会机制的分析。
高帆提出了关系型信用这一概念, 对于理解发生在私人化的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行为有一定帮助。[5] 村庄私人间的借贷被温铁军进一步分为亲朋间互助式与高利贷两种类型, 并且他从理性人的角度分析了高利贷存在的合理性。[6] 上述研究均未发现在强关系的民间熟人信贷与陌生化的高利信贷之间存在着中间形态, 即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 这类借贷行为有着不同于前两者的运行逻辑。在均质化的欠发达村庄, 仪式性消费支出的增长推涨了发生在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的比率。弱关系的民间借贷的运行逻辑及其所依赖的信用体系与社会基础是本文主要回应的问题。
本文从农村金融供给的非正式主体角度出发对农村民间借贷现象进行分析。笔者在山西田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 在向亲戚朋友筹措资金的强关系型民间借贷行为之外, 以第三方主体为联接纽带的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行为也较为普遍。弱关系的民间借贷并不是按照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逻辑计算利益得失, 而是在利息约定以及还款保障等方面都有一套乡土规范, 遵循着互惠与道义的运行逻辑。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的互惠与道义的实现依托于村庄公共信用体系, 而包括仪式性互助与日常生产生活互助两个方面的互助奠定了村庄公共信用体系的社会基础。
二、村庄概况与研究方法
田村位于山西西南山区, 现有200 多户,564 口人, 下辖5 个自然村。村庄坐落在山谷中, 三面环山, 交通不便, 距离乡镇车程一个小时, 距离县城车程两个小时。田村共有耕地3576 亩, 以种植玉米与小米为主, 土壤贫瘠,多坡地, 灌溉不便, 年平均降雨量550 毫米, 容易遭受旱灾,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村民的生计模式为农忙时在村务农, 农闲时则在县城周边打零工, 即务农与打工兼业, 仍属于小农经济范畴。田村的村民因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在外打工所从事的多为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 收入每月两三千元且不稳定。除了不到5%的村民因为在外做包工头或其他生意而在城市买房定居之外, 剩下大多数村民收入相差不大。村里到目前为止没有建楼房的, 大多仍住在窑洞里。田村在行政上隶属于石县, 自从1985 年设立国家级贫困县以来, 石县连续30 年一直都位列其中。2012 年石县人均纯收入为2450 元, 只相当于2012 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1/3。田村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与社会低度分化地区的典型代表, 研究其村庄经济生活对我们理解其他中西部地区村庄情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充分了解村庄整体情况的基础上, 通过入户访谈方式对村民间的借贷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笔者以一个20 户的自然村为分析单位, 对村民借贷的数额、来源、用途与利息等情况进行了问卷统计, 得出如下结论: 除了4 户已经进城定居的,在村的16 户中14 户有借贷行为, 比例高达87 涉及到为儿子结婚的仪式性借贷占75%; 通过亲戚、朋友与本村村民筹集资金的为85 从信用社贷款的有两户, 用于购买汽车与挖掘机, 属于生产性投资。
三、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
农户的金融需求满足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 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为在浙江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摇会 标会 等组织化形式; 另一种为在田村流行的亲戚朋友或村民间的私人借贷等非组织化形式。村民对资金需求的解决除了依靠血缘与趣缘关系形成的亲戚朋友, 一般关系的村民也成为重要来源。学术界对于发生在亲朋之间的借贷行为已有成熟的研究, 笔者则着重分析弱关系的村民之间的借贷行为即弱关系型民间借贷, 并运用公共信用这一概念对其进行解释。总的来看, 田村弱关系的民间借贷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 借贷双方以有权威的第三方主体作为中间人, 双方不直接发生借贷关系。第三方主体作为资金借入方的担保人, 首先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在借入方没有能力或不愿还款的情况下, 由中间人承担连带责任, 代为偿付。此外中间人还需要在村庄中有一定权威, 对于借出方而言, 有权威与公信力的中间人更值得信任。在田村给村民当中间人最多的是一位60 多岁的小学教师, 他与妻子都是有着二三十年教龄的老教师, 两人每月工资加起来有8000 元, 收入在村里属于上层。另一方面, 他对村里的仪式习俗很熟悉, 字又写得好, 村民办红白事大都请他做帐房先生, 他为人公正受到村民的称赞, 在村里很有威信。
第二, 借贷的事项主要是仪式性消费。田村村民之间的借贷主要是用于给儿子结婚建房。特别是2010 以来, 随着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日益凸显的优势地位, 女性对结婚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现在女方一般都要求在县城买套房及两三万元的彩礼。男方的结婚成本一般需要20 多万, 这对于人均年收入几千元的村民而言无法承受, 借贷也就成为必然选择。村民很少因为购买农业机械或做生意等生产性投资进行借贷。在他们看来,同村村民借贷的利率低于正规金融部门, 将资金用于盈利性投资实际上是在占别人便宜, 只有为了解决自己当下遇到的生活困难才属于借钱的正当理由。
第三, 利息较低。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在1% -15%, 要低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3%。虽然从经济收益上看利息较低, 但村庄私人间的借贷具有隐性利息, 即借了别人的钱就要背上因借钱而带来的人情债, 需要通过向对方提供劳工或在可能的条件下向对方提供贷款偿还人情。[1] 不仅借出方可以获得隐性利息, 中间人也能收获隐性利息, 在其遇到困难时借入方有义务主动帮忙。隐性利息有助于降低村民生活风险, 减少生活的不确定性。
第四, 借贷程序简单, 无正式契约。借贷双方通过中间人口头达成关于借款数额与还款日期的协议, 无需签订借款合同, 资金通过中间人交付给借入方。借入方无需提供财物进行担保, 中间人作为担保人, 以其家庭的所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在还款方式上是分期还, 还是一次性还清。若为分期每次还多少都无正式约定, 具有很大的弹性。之所以不需要像正规金融部门那样签订契约并提供抵押物, 是因为还款的保证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的公共信用之上,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的乡土规范确保了按时还款义务的履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
四、互惠与道义: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乡土内涵
弱关系的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化的形式, 在村庄金融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类型的私人借贷行为, 其逻辑不同于陌生化的市场主体间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计算逻辑, 而是遵循着传统乡土社会中互惠与道义的运行逻辑, 具有较低的利率与运用公共规范保证还款义务的履行等特征。
第一,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中的互惠性。所谓互惠制就是一种双方承担义务的制度, 一方做出给予行动后, 被给予的另一方必须给予相应的回馈。同理, 一方不正当的欺骗行为也会导致另一方与之断绝关系。[7](P129-138) 弱关系型的民间借贷不是一次性的市场交易行为, 双方的交往遵循互惠性的接受回馈 原则, 即借入方在获得资金的同时还欠了对方人情, 借出方则附带着收获了人情这一隐性利息, 双方同时处于既接受又回馈的互惠网络中。田村经济分化程度低,富人较少, 有闲置资金的村民一般都还未到为儿子建房娶妻的阶段, 属于暂时性的节余, 将闲置资金借给有需要的村民实际上是在为以后储蓄。当借出方需要为儿子建房娶妻时, 之前的借入方不仅需要还本付息, 还需要根据自身能力主动借款给借出方, 以偿还之前欠下的人情。村民黄元善的儿子2014 年结婚, 7 位之前向他借过钱的村民主动送来了14500 元。在村庄生活中, 人情实际上与货币一样扮演着一般等价物的角色, 特别是对于田村这样货币短缺的村庄来说更是如此。在村民看来, 欠下的人情是必须偿还的, 可以通过提供劳务、农业生产指导或各种仪式知识指导等方式抵偿。与货币不同的是, 人情无法对具体数额进行精确计算,交换原则也是模糊性的, 无法清晰厘定。借入方之所以对偿还人情比较在意是基于本体性良心与社会性面子两方面的考虑。做人要讲良心的理念要求借入方在借出方需要资金时提供帮助, 否则就会背负人情债, 心中充满对借出方的愧疚, 产生很强的亏欠感, 并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 村民的生产生活嵌入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 若借入方在借出方需要资金资助时未进行回馈, 就会遭受忘恩负义 不懂得感恩 自私自利 等负面评价。面子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不讲面子的村民会被其他村民污名化。[8] 村民对借入方不义行为进行社会评价的过程, 也是借入方自我形象管理的过程, 遭到村庄的负面评价意味着借入方做人的失败, 脸面上就会挂不住。借款人的不义行为还会在村庄生活中消极扩散, 以后很难再获得其他村民的资助, 从而被甩出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 沦落为社区的边缘人。乡土社会对借款者的违约行为有着集体惩罚和关联惩罚两种方式, 即运用集体力量对借款者的惩罚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中, 而且体现在社会活动中。[9] 村庄的公共舆论与规范不仅对借入方不义行为有着言语的约制, 而且有着实际的制裁。
第二,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中的道义性。斯科特从生存权的角度分析了东南亚水稻区地主精英在农户遇到生活困难时予以援助的道义合法性,否则农户就会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抵抗。[10](P13-14)这种生存性的道义行为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也普遍存在, 并且国家也会积极参与进来, 设在各地的义仓即为此目的。在田村, 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已经超出了生存性的生活需要, 而主要在于解决结婚建房等仪式性消费的资金短缺。田村属于贫困山区, 传统的生男偏好观念较强, 男女性别比失衡, 当地女性资源稀缺, 外面的女性又不愿嫁进来, 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的优势地位凸显,并不断提高婚姻要价。2005 年男方娶媳妇的一般标准为彩礼两千元, 不用在外买房子, 家庭条件好的会买辆摩托车; 2008 年则变成了彩礼一万元, 还要在镇上花五六万买套房子; 到2013年彩礼增长为两三万元, 还需要在县城花十几万买套商品房, 总共需要20 多万元。上面的数据显示男方的结婚成本呈几何增长趋势, 村民的收入却没有多大增长, 在扣除人情与日常生活的开支外很少有结余, 因而通过借贷筹措所需资金就成为村民的必然选择。
田村不仅经济总体上较为落后, 而且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程度低, 大部分家庭的生计模式都属于务农与打工兼业, 单纯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获得的资金量较为有限, 所以一般关系的村民借贷就成为重要途径。村民黄元善的二儿子2014年结婚, 包括彩礼与县城的房子在内总共花了23 万元, 其中借款64500 元, 共有22 位亲戚、朋友与同村村民借款给他。可见, 借贷行为涉及的主体十分分散。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道义性体现在: 只要需要资金的村民在遇到困难时开口了, 手头有闲置资金的村民就有义务予以帮助,即使对光棍等村庄边缘群体也是一视同仁, 村民只要是社区共同体的一员就都会获得均等化的对待。此外, 道义性还体现在利息的商定上。利息是不固定的且低于正规金融部门, 利息数额的高低取决于借入方的经济困难状况、其在村庄的社会评价以及中间人的威信。一般借出方对那些有困难的借入方会通过较低的利息予以照顾。现在田村村民间的借贷利率大都在一分到一分五之间, 比信用社低一半。借出方不能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考虑, 他会结合借入方的情况对利息做出一定让步, 否则就会遭受社区舆论的负面评价, 被认为不讲情面, 眼睛只盯着钱。
五、公共信用: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乡土依托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具有互惠与道义性, 借贷双方所遵循的不是陌生人之间的理性计算的交往原则, 而是社区共同体内部自己人 的情感原则。不同于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所凭借的私人化的关系型信用,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依托的是村社公共信用体系。这一信用体系使得村民间借贷程序简便, 双方不需要签订正规的契约, 同时又能够确保借入方履行还款义务, 保护借出方的利益, 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公共信用体系的实现建立在村庄社会基础上, 即熟人社会内部的村民间的生产生活互助合作, 包括仪式性的互助与日常生产生活的互助两个层次。
1. 仪式型的公共信用在田村必须公开办酒席的只有结婚与丧事,其他如做寿、庆生与满月等都可办可不办。到目前为止田村只有一户2014 年给母亲办了八十大寿, 大多数村民过寿都只是请亲戚朋友在家聚一下。村民的红白事大都在家里办, 亲朋与村民过来帮忙, 现在还没有出现从市场上请一条龙服务的。主家不需要去请村民, 全村的村民知道后会主动过来, 即使是村庄边缘群体如光棍也有平等机会参与进来, 白事更是如此。在外面打工的村民一般都要回来, 一死百家丧, 白事是谁家都要遇到的, 因而大家需要相互帮忙。田村现在白事还实行土葬, 吊唁、入殓、出殡等各个流程都有专门的仪式规范, 抬棺一般为八人抬, 其他环节如杀猪、洗菜做饭等也都需要不少人手。村民间在红白事上的互助使得私人事务带有社区公共性, 在此过程中大家相互交流情感。仪式事务为村民间的感情聚合提供了平台, 村民间的亲密感与信任感进一步增强, 社区共同体得以维系。红白事的人员安排主家都是请村里的总管负责, 只有那些对仪式知识很了解、有公心的村民才可以当总管。主家不需要为总管支付任何报酬, 不过会为此欠对方一个人情。总管通过垄断仪式知识不断积攒村民欠下的人情, 成为在村庄中有威信的民间精英, 并通过社会赋权得以在村庄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村社共同体的维系离不开这些内生的治理主体, 他们运用地方性规范调解纠纷、和谐社会关系, 进而维护乡土社会秩序。这些有威信的民间精英不仅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而且也因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为村民所信任, 在村民间的借贷行为中成为中间人, 村民大都会买他们的帐。田村70 岁的老支书田有声当了20 多年的村干部与总管, 平时村民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来找他, 在路上遇到也会喊他声当家的。田支书在村里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也很愿意为农户提供包括充当中间人在内的各种帮助。
2. 生活型的公共信用
互助型村社共同体的形塑与再生产不仅体现在重大人生节点的仪式性事务上, 而且在很多超出个体家庭承受能力之外的日常生产生活事务上也同样很突出。
在田村, 建房、红白事、农业生产等各种事务大都依靠村庄力量完成, 市场的渗入程度很低。田村三面环山, 与集镇、县城距离较远, 交通不便, 而很多生产生活事务又具有紧急性, 因此限制了市场力量进入的可能性。村民间日常生产生活的互助是多方面的, 不仅包括农业生产、建房的帮工, 还包括相互借用农用机械、生产工具乃至居住的窑洞等互助行为。村里没有理发室、浴室等服务场所, 这些基本服务都是依靠村民相互帮忙完成的。多元的互助合作不需要货币作为支付媒介, 降低了村民的生活成本。以建房为例, 村民一般只需请两三个大工负责建炕、放线这些技术性较强的事务, 搬砖、打石头这些劳力活一般都是其他村民过来帮忙完成, 平均一天会有七八个村民来帮忙。建窑洞通常需要一个多月, 如果按照市场价请小工算, 一天的工资为一百三四, 依靠村民的帮忙就能够节省10000 元左右的开支。这种多元的互助合作为村民间的资源共享提供了便利。村民所具有的劳力、技术、生产工具与居住场等对其他村民也是可利用的资源, 使得这些资源在村庄生产生活中具有超出个体与家庭范围之外的公共性使用价值。而且不同种类的知识、劳务与物质资源均可通过人情这个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 如在村民间的借贷中借入方就可以通过为借出方提供劳务偿还欠下的人情。
村民间的互助不仅解决了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问题, 也加深了人们的感情,创造、维持和强化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 从宏观上看互助起到了凝聚与整合乡村社会的作用。[11]村民在生产生活的互助合作中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超出个体能力之外的事务, 获得帮助的村民不仅会在接下来的生活中积极回馈别人, 而且对其他村民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这一亲密情感有助于化解平时的小积怨、保持和谐关系, 从而使得村民间的熟悉与亲密感进一步增强。乡土社会的熟悉是从长时间、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进而从熟悉里产生信任。[12](P10) 村庄充满了人情味, 这使得村民仍然有着稳定的面向村庄的生活预期, 村社共同体得以维系, 进而公共的集体信用体系得以保持。在村民间的借贷行为中,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的乡土观念成为舆论规范。倘若借入方悖离公共规范的要求,就会遭受负面的社会评价, 受到其他村民的孤立与排斥, 在需要钱时就很难再借到, 而且其他事情上也不会有村民帮忙, 沦落到社区的边缘位置, 对自己以后在村庄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
六、总结与讨论
村庄民间借贷作为村民抵御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到现在一直普遍存在。村民的收入一般可以保证日常生活的维持, 但积蓄不多, 在遇到重大人生节点上的礼节性开支如为儿子建房娶妻时, 借贷就成为村民的必然选择。随着打工潮的兴起, 村民的收入相较集体时期有了很大增长, 但家庭生活开支也相应提高,特别是人情往来支出, 田村一般关系村民间的随礼从5 年前的二三十元涨到了现在的100 元, 导致家庭积蓄很难增加。一方面村民积蓄难, 另一方面结婚建房等仪式性事务的费用也呈几何式增长。田村2005 年结婚的要求为两三千元彩礼,不需要买房, 现在则涨到彩礼两三万, 还要在县城买房。这主要是因为田村属于欠发达地区且男女性性别失调, 女性在婚姻市场的优势地位凸显, 提高了她们在婚姻中的要价权。
理论上村民对资金需求的满足有正规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两种渠道, 实际上一般村民既不愿意也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资金。农户的借贷主要用于应对生活风险, 因而预期收益率较低以及农户从正规金融部门借款的交易成本高这两个方面导致了农户对正规金融的需求抑制。[5] 小农经济下农户本身经营与居住的分散性、收入受市场影响较大、缺乏可靠的信用以及农户的弱势谈判地位使得农户无法与正规金融部门对接。[6]
当正规金融部门被排除后, 农户的借贷只能借助于非正规的民间形式, 如依靠私人化的血缘、趣缘关系的亲戚朋友, 或依靠社区组织的摇会标会 以及一些灰色的地下钱庄等。作为典型的均质化和欠发达村庄代表的田村, 单纯依靠某一方面的力量如亲戚朋友无法完全满足资金需求, 导致借出方的主体高度分散, 弱关系型民间借贷也就成为常规化的形式。弱关系型民间借贷借助于有威信的中间人完成, 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理性计算行为, 而且带有社区内部自己人之间的互惠性与道义性借出方在利息的商定上做出一定让步, 借入方则保证按时还款。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程序简便, 双方不需要签订正规的借款合同, 借入方也不需要提供抵押物, 中间人作为担保人, 在借入方未能还款时承担连带责任, 代为偿付。互惠性与道义性的弱关系民间借贷的实现依托于村庄的公共信用体系, 这是一种集体信用体系, 个人因为属于社区成员而有资格获得保护, 其形成建立在村社共同体这一社会基础之上。田村村民间的多元的互助合作, 包括仪式性互助与日常生产生活互助两个方面, 增强了村民相互间的熟悉与亲密感, 保持了村民面向村庄的生活预期, 从而使温情脉脉的乡土社会得以维持与再生产。
目前政府与学术界对民间借贷持较为否定的态度。农村民间借贷无序化对金融秩序有破坏作用, 因而需要加强政府监管。[13] 我们需要辩证与区别地看待民间借贷行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民间借贷多属于盈利性与投机性的生产投资, 这种类型的民间借贷确实具有很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需要政府力量介入加强监管。然而在广大欠发达的中西部村庄, 村民生活性的金融需求较为普遍, 正规金融部门却很难与村民的需求相对接, 非正规的民间借贷也就成为必然选择。在均质化的欠发达村庄, 村民借贷除了依靠关系型信用的亲戚朋友, 依靠公共信用支撑的弱关系型民间借贷也成为常规形式。村社共同体发挥了保障村民生活、维持村庄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作用, 属于内生的低成本社会保障体系。如何挖掘村庄内生金融资源, 建立村民间的金融合作体系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李似鸿提出的乡村金融自治, 即以村落为基础设立农户资金互助组织, 以满足整个村组成员紧急的资金需求, 以此引导并实现村民自治,[14] 是政府部门可以借鉴的用于化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