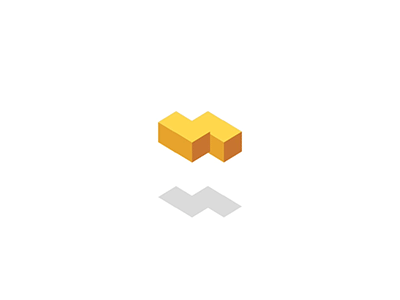自从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直接适用宪法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做出司法解释以后,又发生了一些以推动宪法实施为目的的案件和事例。(注:这些事例包括:
(1)2001年8月,山东青岛3名高中毕业生状告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造成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平等一案。该案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属受案范围而被驳回。
(2)2001年12月,四川大学生蒋某引用宪法平等权条款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限制身高歧视案。该案因雇工一方在招工广告生效前自行修改录用条件。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3)2009年,四川大学生用宪法平等权条款状告峨嵋山公园门票价格歧视案。该案被法院判为败诉。
(4)2009年4月,因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打死一案而引发三位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要求对国务院《收容遣送办法》实行违宪审查。
(5)2009年7月,浙江杭州和金华市分别有116名和1300多名市民联名提出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 由这些案件和事例引发的宪法实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为保障中国宪法实施,可以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
一、西方宪法私法化的理论与实践——以德国和美国为例 宪法私法化是当代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谓宪法私法化,就是指宪法在私人关系领域间接或直接适用,以解决公民之间涉及宪法权利的纠纷,从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宪法基本原理上说,宪法是规范国家权力,以“限制政府不得为非”,从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根本目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宪政国家坚持传统宪政理论,不承认宪法适用于私人领域。
认为除非具备“国家行为”(State action),宪法对私人间的诉讼缺乏直接影响。纯私人之间的争议,完全由国会或各州议会的立法及法院的判例法加以解决,宪法只适用于公民与联邦政府或各州政府机构之间的争议。
(注: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9页。)可见,宪法就法律关系讲是调整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法律,其规范对象是“国家行为”,其产生的原意为限制政府权力,而非规范私人行为。
这是传统的宪政理论。但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宪政国家主张宪法可适用于私法领域,以解决涉及宪法的私权之间的纠纷。
宪法私法化是适应人权保障要求的一种现代宪政发展趋势。
(一)德国的宪法私法化问题 宪法私法化理论首先产生并实践于德国。早在1919年《魏玛宪法》时,就有学者主张,宪法中的基本人权规定应适用于全部社会生活。
该宪法第118条第一项和第159条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以劳工为目的结社自由,不得以私法予以限制。这两项规定禁止“任何人” 的契约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进行限制,宪法规范公然调整私法关系。
这在制宪史上开创了宪法基本权利可涉入公民私法领域的先例。1949年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并没有直接赋予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以私法性质,而是保持了公法的纯粹性。
宪法私法化是在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这项制度的创立,源于二战以后德国对法西斯践踏人权的恶行进行的深刻反思。
宪法虽然主要是规范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但公民个人也不是没有侵害他人宪法基本权利的可能。如果依传统的宪法立场严格限制宪法的适用对象,会回避侵犯宪法权利的现象,自缚手脚,造成人权保障的重大缺失。
这样可能变相鼓励国家借私权行为,以逃避国家应担负的责任。但是也担心,如果将宪法全面适用于私法领域可能导致公权侵入私权,会破坏私权自治的传统,所以宪法适用私法又是非常谨慎,且对适用范围和程度尽可能加以限制。
(注:法治斌:《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台北:月旦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宪法是否适用于私法关系,这在德国曾引起激烈的讨论。
积极主张宪法应适用私法的联邦劳动法院大法官Hans Carl Nipperdey 与Walter Leisner认为,对于私法规定不足,且无其他法律可依据,而保障人权又必须时,法院可直接引用宪法的规定以解决私人之间的争议。 (注:Lewan ,supra note 166at 573.)1950年,Hans Carl Nipperdey 在《妇女同工同酬》一文中主张,宪法条款在私法关系中应当具有“绝对的效力”,在私法判决中可以直接被引用。
因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是“最高规范”,如果它不能在私法中被适用,基本权利条款将沦为“绝对的宣示性质”的具文。(注:参见王涌“论宪法与私法的关系”,引自“宪法文本”网站。
)古典的宪法基本权利仅仅是消极地对抗国家权力,维护个人自由的领域。 但是,保障社会、经济弱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权、受教育权、平等权等,这些权利并非消极性权利,而是有待于国家采取措施予以实现的积极权利,故而法院可直接引用宪法规定,不是必须依赖民事法律的引用基本权利在民事案件中得以实现。
尽管Nipperdey 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批评,(注:Nipperdey 的直接效力说立刻遭到法学界的批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1950年5月3日W.Schmidt-Rimpler 等提出的一份《波昂研究所评论》(Bonner Instituts-Gutachten)。
他们认为,基本法的序言明确表示基本法的制定是为“国家之生活有一新秩序”,说明它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只以限制国家侵犯为主,并非规范私人之关系。至于基本权利作为“最高的规范”,尽管具有“一般评价标准”,亦即“确认合宪的最高正义思想”,也不能在私法关系中直接适用,至多通过“民法解释”的途径,实现基本权利中所隐含的“一般评价标准”。
) 但是,劳工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毫不犹豫地采纳了Nipperdey 的观点。1954年德国联邦劳工法院在劳动关系领域直接适用宪法。
案例是在一起雇佣劳动案件中,雇主基于雇员发表了某种政治言论而将其解雇。联邦劳工法院认为,雇员有权援引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对抗雇主,因而劳工法院判决雇主解雇雇员的行为违反基本法。
法院判决认为,虽然并非全部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都只是针对国家权力的“自由权”,还有一连串重要的基本权利规定,皆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原则,某些宪法的基本价值进入了法律的基础构架。这些原则对于国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意义,因此,所有私法的协议、法律行为及作为都不能与之相抵触。
(注:参见王涌“论宪法与私法的关系”。)此后,联邦劳动法院根据上述立场在劳动关系领域做出一系列重要的判决。
因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宪法权利,从而禁止私人雇主基于性别的工资歧视;当雇用合同条款不适当地限制了雇员的诸如婚姻权和自由择业权等特定的基本权利时,这些限权条款也被判定无效。(注:案例是德国Nordrein-westfalen邦的一家疗养院,原告是该疗养院的实习护士。
根据该邦有关的规定,实习护士不得结婚,否则,她必须在结婚的当月离职。原告在求职时曾表示接受这一义务。
后来原告结婚,被告宣布该实习生劳动关系解除。原告起诉请求法院确认此项约定无效,三审均获胜诉。
)然而,由Nipperdey 创造和劳工法院确立的宪法对私法的“直接适用”理论没有用被联邦宪法法院完全采纳,联邦宪法法院采取了一种折中的“间接适用”(indirect ect)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宪法基本权利系针对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而设,基本权利的实现首先应以国家立法的方式为之,而不能直接适用于私人关系,否则宪法无异于完全取代立法者的地位,更使私法的独立性受威胁。
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如自由、平等、人格尊严,应视为全部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或目的,这样可以充实民法中若干原则规定或不确定概念的内容,使之具体化、实质化。在公民个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中,宪法性权利只限于对私法原则产生一定“影响”(influence )而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宪法精神只照耀着私法体系,并且影响着对私法规则的解释。
由此,私法规则应当在相应的宪法规范的基础上加以解释适用,形式上仍适用规范私人关系的民法规定,实际上依宪法的价值,在权衡客观事实及相关利益而做出判决。概而言之,宪法的规定需凭借民法的原则性条款进入私法领域,不得舍弃民法,而直接引用宪法。
(注:参见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Peter E.Quint 著“德国宪政理论上的言论自由和私法自治”一文。它是研究德国宪法私法化最全面、最权威的文章。
余履雪博士和我已将其译出,并将发表于《中外法学》,本文的很多观点引自此文。 另参见Horan ,Contemporary Constitutionalism and Legal R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Individuals,p.251.)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私法化方面最著名的案例是1958年Harlan诉Luth(抵制电影案)。
这是个典型的民事案子,纠纷发生在民事行为个体的电影制片商与Luth之间,诉讼的理由是商业利益受损要求保护。按传统的宪法理论,宪法没有任何适用的余地。
但是,Luth以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为由,提出了宪法诉讼。这就把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变成一个宪法争议。
一方是民法上的经济权利,一方是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法院保不保护私人冲突间的宪法权利? 法院认为,由于宪法权利的极端重要性使得这些权利不应仅仅被看作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应当在社会的所有场合被奉为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一般原则,民事个体以及私人团体之间的私权法律关系当然也不例外。
基于以上考虑,联邦宪法法院毅然采取宪法性权利作用于私法领域的立场。(注:参见Peter E.Quint “德国宪政理论上的言论自由和私法自治”。
)在1950年代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确立宪法私法化方向以后,1973年在Soraya一案中又建立了“宪法理由之诉”。(注:即允许民事个体基于其宪法权益向另一方民事个体提起诉讼。
)即德国宪法对私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被告有权以其享有的宪法权利对抗司法机关的不利裁决;而且宪法对民事主体之间关系的影响,要求司法机关主动创立一种宪法理由之诉讼,它是基于基本法第
1、2条对“人格权”的保护,明确肯定在民事个体之间的赔偿诉讼中可采用此种手段。普遍的人格权在基本法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高于一般的公民权,所以,这一宪法权利不仅可以用来制止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而且可以用来对抗个人。
如果不建立这种诉讼,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就可能受到来自其他公民的侵犯而得不到保护。因此,宪法必须承认这种宪法诉讼。
(注:参见Peter E.Quint “德国宪政理论上的言论自由和私法自治”。) 宪法私法化的案件一般涉及两种情况:一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产生纠纷的民事权利同时又是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公民之间这两种民事权利冲突先在普通法院诉讼后再上升到宪法层面的诉讼。
宪法诉讼就需要法院对公民之间受到侵犯的个体宪法权利与实施侵权行为一方的宪法权利进行权衡,决定优先保护哪一种宪法权利。二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主要是人格权受到其他公民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的宪法权利可以构成一种“宪法原因之诉的诉因,提起宪法诉讼,请求保护其宪法权利。
”宪法适用于私法关系是非常审慎的。法院要考虑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要考量宪法价值在私权法律关系中的效力大小,因此涉及一系列因素:当事人的宪法权利受侵犯的程度;(注:德国的宪法是否侵入私法,最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公民宪法权力的危害程度,而不是危害行为的来源上。
美国则主要考虑后者,看侵害来源是否是“国家行为”。)当事人主张宪法权利的动机;对公民宪法权利造成威胁的行为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他可能享有的与被害人冲突的宪法权利或者其他权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