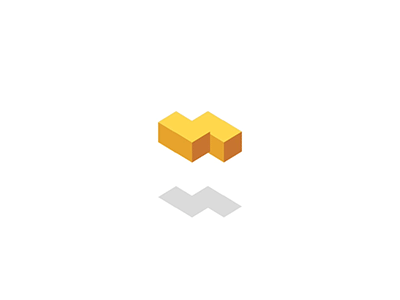摘 要:目的论解释在法律解释中的影响日益突出,与自由法运动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目的论解释功能的界定,对于控制目的论解释被滥用的危险非常重要。目的论解释的基本功能不是补充刑法漏洞,而是具有承载刑法价值评价的基本功能。对于刑法条文中需要补充价值的不确定概念,诸如模糊性概念、多义性概念、规范性概念以及概括性条款等,只能通过目的论解释才能获得其真正含义。
关键词:目的论解释 规范性概念 概括性条款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2-0064-11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按照人类共同生活的公正的和谐的秩序原则之意义,理解法律规范既定的含义。因此,法律解释首先是探求法律条文可能的字义,“任何解释都从规范条文出发。文义是所有解释的首要的出发点。因此,对法律文义谨慎地认识和分析是适当解释的首要前提”。 ①这种借助于法律条文的可能的字义,作为划定法律解释界限范围的方法是最古老的法律方法。人们在与法律的交往中,基于对法律保护的信赖,自然会坚持法律条文的可能的字义的一般理解,这也是任何解释的基本出发点。在法学领域,随着概念法学以及形式法治思想的影响,这种理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仅从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就可以看出,法条解释界限是受到字面含义界限的约束的。……撇开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不论,以条文的字面含义限制条文解释实际上也是正确之举。因为立法者只能够通过文字来表达规范命令”。 ②但是,“可能的字义”界限理论,一方面来自于法诠释学理论的挑战,认为其是不可能担负解释的界限,彻底否定其作为解释界限的理论意义,甚至企图利用类型理论取而代之; ③另一方面立足于语言分析哲学的立场,积极为“可能的字义”界限理论之可能性提供理论支持,力图维护“可能的字义”作为法律解释界限,特别是刑法解释界限的权威性。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可能的字义”界限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例如对于法律中的不确定性概念,它的作用就极为有限。因此,目的论解释随着目的论概念被引入法学理论,逐渐为人们所注目。19世纪以来,耶林的目的法学思想引导了法学方法论的革命,用目的取代逻辑,目的论概念成为解释法律时至关重要的、权威的因素。特别是针对在法律内无可争议地存在的模糊性规定,“要求作为‘立法者的助手’的法官对待法律要有一种‘进行思考的服从’,这是必然的结果”。[德]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据此,“法官不能把案情按照逻辑学的方法纳入各种秩序的概念里,他必须――从目的论上――探讨,按其社会道德的和实际的目的,法律的规则是否可以应用到案情上”。前引④,第219页。 这一思想在后来的自由法运动中更为尖锐地凸现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价值评价与法益理论通过目的论概念融汇成为一体,成为刑法实质化思潮中的核心范畴,在实践中彻底改变了刑法解释的现实图景。因为目的论解释理论发展的原动力直接来自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法运动(die freirechtliche Bewegung)。正是受到耶林的目的论思想的深刻影响,当时德国有很多法学家和法官反对概念法学的教条理论,主张法官积极行使自由裁量的权力,通过自由的法律发现,获得符合事物本质的正义裁判。自由法运动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时,不再受法律所使用语词的可能的字义的束缚。因此,目的论解释在法律解释中的影响日益突出,这与自由法运动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诚如当代著名法学家昂格尔指出:“与日益增加地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标准相结合,司法机关日趋转向目的导向的法律推理模式……这一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因素就是,司法机关逐步承认了‘自有法律运动’及‘利益法学’的理论家们所提倡的方法和观点。”[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可见,目的论解释发展的理论动力正是自由法运动。
如果说在法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性、自治性、公共性和实在性的法律规则体系的形式法治,注重实现形式正义的价值追求,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并仍在长期发生影响,与之相应,在进行法律解释时,首先注重的是将法律条文可能的字义作为优先原则,但是,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法运动等现实主义法律观念的兴起,日益强调目的论概念导向的法律方法,追求实质的正义价值,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不断侵蚀形式法治所坚持的法律普遍性。作为实质法治的主要法律方法的目的论解释尤其引人注意,“目的解释所具有的优点,包括克服法律的封闭性与僵化性、确保法律推理的合理性等,都是以牺牲规则的权威性和意义的固定性为代价的”。陈金钊:《目的解释方法及其意义》,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因此,目的论解释的功能的界定,对于控制目的论解释被滥用的危险显得非常重要。
在这种情形下,法官自由的法的发现活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因此,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一现实,通过合理的方法运用与恰当的制度设计,对法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自由的法的发现进行理性的限制,将因此引起的那些阻碍实现刑法明确性的不利因素减小到最低的限度。如此一来,目的论解释始终与刑法中自由的法发现联系在一起,目的论解释的功能界限与此须臾不可分离。关于法官在刑法领域自由的法发现的理论探讨,参见王祖书:《刑法中“自由的法”发现及其限制》,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4年总第2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22页。 “然而与此同时,法律适用者也获得了创造、独创的自由,法律适用者应该对此自由有所意识,并且应当公开地实践”。[德]英格伯格・普珀:《法学思维小课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目的论解释的重要功能即在于此,也就是目的论解释只有在其作为刑法自由发现的方法时,因其所承载的刑法价值评价的基本功能,才可能成为各种解释方法之桂冠。“今日对于目的论解释方法如此尊崇的原因在于,这种解释方法给予法律人最大的自由空间,让‘自己的理性(seine eigene Vernunftigkeit )’得以发挥作用。”NK-Hassemer/Karel§1 Rn.114.转引自前引⑨,第69页。 因此,为了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实现刑法的明确性,目的论解释方法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 二、目的论解释的基本功能定位
关于目的论解释的基本功能,有学者结合刑法实质化的思潮,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且认为:“从一开始,目的解释就被当作堵截刑法漏洞的主要的解释方法,它的基本功能是确保刑法之网的严密性与开放性,以堵塞不断涌现的处罚上的可能的‘漏洞’。”该学者进而指出:“法学中对目的因素的强调,始终是与法律续造任务联系在一切。”劳东燕:《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第81页。 可见,该学者将目的论解释的基本功能立足于法律续造的方法论领域,将其界定为填补刑法漏洞的法律方法。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因为从本质上看,这一结论一方面为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允许,根据该原则,所谓的刑法漏洞不同于其他如民法等领域的漏洞,允许通过目的论解释的方法进行法律补充,这是为刑法所严格禁止的,在此有将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律混为一谈的嫌疑。另一方面,该结论严重误解了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理论背景下的刑法实质化的主要问题,从表面上并不能看出是“对目的因素的关注与强调”,或者“目的在法律适用中重要性的提升,与法律实质化思潮之间存在莫大的关联”。前引B11。 所谓刑法的实质化或者法律的实质化的主题是价值评价进入了法学领域,并逐渐为法学理论所承认。而这一过程在笔者看来是通过目的论概念作为媒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目的论解释具有承载刑法中价值评价的基本功能。
首先,从法学方法论的视角来看,价值评价是其关注的理论基本问题。在法学理论中对价值评价是否承认存在严重的理论分歧,对此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颜厥安教授进行了很好的理论梳理,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91页。 笔者在此仅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作一补充完善之阐述。其一,颜厥安教授将著名法学家凯尔森作为“价值不可知论”在法学界的重要代表,他在思考对法学中评价因素的几个主要见解时指出:“第一种见解认为,价值判断确实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对于价值的高低优劣,并没有一种客观的方式或标准可加以决定,价值的正确性与否是理性所无法认识,而只是透过意志的作用来加以决定。这是一种典型的价值(伦理学)不可知论(ethischer Nonkgnitvismus)。Hans Kelsen是其在法学界的重要代表。”前引B13,第89―90页。笔者认为颜厥安教授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凯尔森明确指出:“法律规范之可被适用,不仅在于它由机关所执行或由国民所服从,而且还在于它构成一个特定的价值判断基础。这种判断使机关或国民的行为成为合法的(根据法律的、正当的)或非法的(不根据法律的、错误的)行为。这些是特定的、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对一定行为是合法或非法的判断中所包含的价值表语,在这里,就被称为‘法律的价值’,而对一个法律秩序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判断中所包含的价值表语,则称之为‘正义的价值’。宣称法律价值的陈述是客观价值判断,而宣称正义价值的陈述是主观价值判断”。前引B15。 凯尔森反对的是与“法律的价值”不具有同质性的主观的“正义的价值”,他赞成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因为“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具有客观性。法律价值的存在是在客观上可以验证的”。前引B15,第52页。 与之相反,“正义的价值判断,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而这些意识形态,并不是像法律上的价值判断那样,是与一个确定的社会现实并行的”。前引B15,第53页。 由此可见,凯尔森虽然在理论上认为必须将何为法律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加以严格的区别,但是其并不认为在法律的实践中,可以完全排除价值评价。相反,他认为在具体的法官适用法律的实践中,法律的判断与法官个人的价值评价是密不可分的;不仅如此,在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时也或多或少涉及法律的价值评价,因此不能将价值评价从法学领域完全排除。其二,法学中的“价值不可知论”的真正代表当推美国著名法学家、被誉为“伟大的反对论者”的大法官霍姆斯,其基本立场就站在反对当时的自由法运动的思想阵营,反对有绝对的价值之存在而可以被客观地认知的思想。其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自然法》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一位中世纪的骑士而言,如不承认其妻为上帝所创造的最美丽的女性,他必与之宣战,而自然法者的心态与中世纪的骑士的心态相同,如不承认其所主张之自然法为绝对、最高、最具普遍正当性者,他必与之争论。”O.W,Holmes,Nature Law, Holmes ed.,The Collected Legal Papers,N.Y.1921,p310. 其三,肯定法律中存在价值评价的杰出代表应是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他在其经典著作《法哲学》中特别关注价值评价的问题,这可以从该书的第一章“现实和价值”、第二章“法哲学作为法律价值的思考”等题目中看出他对法律中的价值评价理论的关注程度。拉德布鲁赫也正是以价值相对主义在学界留名,他明确指出:“法律只有在涉及价值的立场框架中才可能被理解。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涉及价值的事物。……法律理念自身,根本性原则以及法律现实的共同价值尺度,都属于评判价值的立场。”[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他从法律思维的立场进一步指出有三种关于法律的思考:“涉及价值的思考,是作为文化事实的法律思考――它构成了法律科学的本质;评判价值的思考,是作为文化价值的法律思考――法哲学通过它得以实现;最后,超越价值的法律思考,是本质的或者无本质的空洞性思考,这是法律宗教哲学的一项任务。”前引B20。 这一价值相对主义思想终其一生并无改变。正是经由以拉德布鲁赫为代表的法学家的不懈努力,价值评价的思想才成为法学理论中的主流思想,正如拉伦茨所指出的:“在法律判断中经常包括价值判断,例如决定特定行为是否有过失。当法官决定采纳类推适用的方式与否,当法官‘衡量’相互冲突的法益或利益时,或者,当法官考量生活关系的新发展及改变时(与以前相比,法官作此种考量的机会要多得多),他们都必须要以价值判断为基础。”[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而且,拉伦茨在其经典的著作《法学方法论》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就是:“由‘利益法学’到‘评价法学’”,这个标题恰当地概括出20世纪法学方法论发展的基本方向。可见,拉伦茨眼里的法学方法论就是价值评价的法学方法论。 其次,也必须明确的是,价值正是通过目的论概念才得以进入法律规范中。“价值是如何进入法律规范中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法律规范的形成,自然是法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对此,维亚克尔教授认为:“20世纪法律演进的两个主导趋势是:就法秩序与社会事实关系如何之见解的转变,以及对实证法秩序之社会伦理责任的省思。前者植基于法律见解的自然主义化、向直接纳入社会事实突进,以及社会事实对实践责任提出的任务;后者的基础则在于,重新尝试藉实证的法律论证来超越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7页。 可见价值与事实在法律规范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前文已述,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的价值哲学对于刑法中的目的论概念的建构影响巨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价值正是通过目的论概念才得以进入法律规范的,因而法律规范便具有了目的论特征。任何法律规范均是基于一定的目的而形成,这不仅体现在法律规范的构建之初,也显现于随着社会变迁法律规范因之演进的历史进程之中。在此意义下,每一个法律规范都与其承载的规范目的相对应,每一个法律规范的意义都由其具体的规范目的所决定,于此,可以认为法律规范一直带有目的性。这也可以从法律规范的要素――法律概念的形成中获得印证。例如魏德士指出:“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材料。这是因为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由‘当为语句’构成,他们必须服务于特定的规范目的,并按照立法者的‘社会理想’对国家和社会进行调整。法律概念也承担着法的调控任务,也受制于目的论。日常用语中描述性的‘观念概念’就这样演变成了规范性的制度形成工具。因此,是规范目的决定了法律概念的功能,而不是相反。”前引①,第94―95页。 这种目的性在所谓模糊性概念、多义性概念、规范性概念以及概括性条款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中,表现得自然尤其明显。因而,可以看出法律条文的意义正是以规范目的为基础,规范目的对法律条文意义的形成又具有决定性。而这又必须通过目的论解释才能完成,在此正凸显出目的论解释的重要性。甚至,德国学者Tipke教授认为:“法律解释应取向于法律目的……是故,将文义、历史/发生、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并列是不正确的。一个文义、历史/发生、体系解释如果不回归于法律目的是不合格的。文法学、起源学、体系学都只是确认法律目的之工具。”Joachim Lang,in:Tipke/Lang,Steuerrecht,17.Aufl.,2002, §5 Rz.50f.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页。 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对刑法的解释,总是从刑法用语的含义出发,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结论。如果进行语义解释还不能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结论,就要采取其他解释方法,直到得出符合刑法目的的解释结论为止。”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再次,目的论解释具有价值性特征。目的论解释的任务即在于探求刑法条文规定的基本意义,即追求法益的保护,从而形成与维护人类社会生活的法益秩序。而这种刑法的目的论解释绝不仅是徒具语言形式的东西,它有其志,更有其意义,它追求的是规范目的的实现,它关注的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法益价值,因而是以价值评价为其基础的。在此,人们只是通过目的论解释确定某个目的,而该目的又是由某种法益的核心价值所决定,针对此种目的以及相关法益价值的决定正是刑法的意义之所在。诚如魏德士所强调:“规范目的是一切解释的重要目标……任何解释都应当有助于实现规范内容所追求的目的。其他解释标准也应当服从于这个目标;它们是解释者必须借以认识规范目的的工具。”前引①,第321页。 因此在所有的刑法解释方法之中,目的论解释方法最具有价值性特征,这种价值性特征对于解释刑法规范,特别是其中所谓模糊性概念、多义性概念、规范性概念以及概括性条款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作用巨大。因为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背后,蕴含的是法益的冲突,由此引出的法益权衡自然需要有一套价值体系作为依据,在此,法律概念的目的追求具有了“价值取向化”的特征,于是法律规范的目的论特征与目的论解释的价值性特征密切联系起来。“日益增长的,对立法者之社会动机与刑事政策评价的分析,鼓舞德意志刑法释义学从事目的论解释与概念形成,虽然相应于法定犯罪构成要件在法治国中的意义,其进行在理论上自较利益法学严格。此种解释理论就其逻辑前提而言为西南新康德学派的门徒,其目的,质言之,解释与概念形成的目的规定(就此,新康德派的形式主义本身并未提供实质的法价值),必须求诸相对主义伦理学之内存的生命与社会价值。”前引B23,第552页。 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正是因为目的论解释的存在,才使刑法解释乃至法律解释亦具有价值性特征。而这一点从价值判断在目的论解释中的重视程度被直接反映出来,例如,拉伦茨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有关目的论解释的内容主要是探讨“价值判断”的问题。可见,目的论解释的价值性特征使其成为实现实质正义的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刑法中目的论解释的基本功能不是补充刑法漏洞,而是承载刑法价值评价。但是这也使目的论解释成为一柄双刃剑,具有滑向任意解释的危险性。诚如魏德士在对德国纳粹时代司法进行深刻反思时指出:“法的价值联系具有决定性。任何法律秩序都以特定的价值秩序为基础。任何法律规范都回溯到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法哲学对法的基本价值的回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换。……在过去和当今的极权主义制度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法的名义下的重大犯罪的教训表明:一种法律秩序、一种法学和一种司法倘若不意识到不可放弃的基本权利和人权的实质性的价值秩序,就不可能成为当时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工具。”前引①,第423页。
因此,必须重视可能的字义作为法律解释界限的作用。可能的字义范围就是法律解释的边界,逾越该界限范围就已经不是在解释法律,而是进行法律的续造。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赛克曾明确指出:“条文的词义是解释的要素,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将‘可能的词义’视为最宽的界限。该界限的另一端是什么意思,已经是法适用问题,已不能从方法上再称之为解释。”[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尽管这一观点面对着立足于法诠释学立场的严峻挑战,但是其通说的地位亦很难撼动。甚至置身于法诠释学阵营的拉伦茨也必须承认:“字义或者是由一般的语言用法获得,或是由法律的特殊语法,或是由一般的法学语法中获得,无论如何,它在解释上一方面可以当作第一个方向指标,另一方面也可以――依当时或今日的语言理解――划定解释的界限。可以说,它已经划定进一步解释活动的界域。”前引B22,第204页。 究其原因,法律解释必须在可能的字义范围之内,如此通过可能的字义界限指示法条规范的内容范围,进而有助于确定法官解释法律权力的界限。这不仅是基于法的安定性的基本要求,对于刑法而言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直接体现。因此,只有通过可能的字义标定法律解释活动的范围,才能够进一步通过目的论解释在该范围内进行规范目的的发现与确定工作,直至获得合理的解释结论。由此可见,目的论解释的价值评价功能的实现,自然必须以可能的字义范围为前提。这也印证了罗可辛教授所言:“一个正确的解释因此必须永远同时根据原文文字和法律的目的。仅仅满足两者中的一个标准是不够的。”[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6页。 三、目的论解释基本功能的适用范围
二战结束后,伴随福利国家的兴起与发展,在诸多方面影响了法治的现实图景。昂格尔教授认为有两种直接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其中一种影响即表现为大量的无固定内容的不确定的命令和一般性的条款,迅速地体现于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条文中;另一种影响则体现在司法领域,人们的价值关注开始从形式公正向程序或实质公正的转变,从形式主义的三段论推理向具有目的性导向的实质的法律推理转变。前引⑥,第187页。 这两种转变一方面使形式正义的语言功能受到冲击,已经不再将语言作为稳定而明确的范畴,法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另一方面目的论导向的法律思维以及对实质正义的关注逐渐占了上风。这些自然成为目的论解释发挥其作用的重要领域。在刑法领域自然也存在大量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需要通过目的论解释进行价值评价,这类概念一般包括模糊性概念、多义性概念、规范性概念以及概括性条款等,以下分别予以阐述。
(一)模糊性概念
模糊性概念在理论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模糊性概念,是指由核心概念与边缘概念所组成文字意义上外延不确定的空间概念,这是一个有待明确的概念的语义空间。例如,德国学者齐佩利乌斯就认为:“具体的语词通常情况下都有一个包括各种可能语义的空间。……从而,法律解释的任务只能是,在特定法律语词的语义空间之内,选择那些就使用了该法律语词的特定法条而言可最恰当地赋予该法律语词的涵义。”[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7页。 这就意味着,在概念的核心区域必须具有一个已经被公认的语词意义,使得在所有情形下都能获得同一个解释结论。与之相反,在概念的边缘区域虽然存在一定的可能有的意义,但并不是绝对必须具有的意义,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区域模型”的模糊性概念。有很多学者为此使用了著名的像日蚀中的“半影(penumbra)比喻”,来喻指语词意义中的模糊的边缘区域。例如本杰明・卡多佐在1921年撰写的名著《司法过程的性质》中这样写道:“在边缘地带,在半影区域(penumbra),争议开始出现。”Benjamin N. Cardozo,The Natuer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21,p130. 格兰威尔・威廉姆斯在1945年的一篇著名的法理论文中也使用了这一比喻:“因为法律必须使用语词表述,但是语词存在一个不明确的阴影区域(penumbra),因此它总是会引起某些边缘情形的出现。”Glanville Williams,Law and Language,Law Quarterly Review,1945,61,p293. 哈特继受了他们的思想指出:“每当我们把特定的具体情况涵摄于抽象的规则时,总是会同时出现具确定性的核心以及值得怀疑的边缘。这使得所有的规则都有着模糊的边缘,或者说‘开放性结构’。”[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拉伦茨认为:“在各种不同的意义可能中,如果其中一种较他种的适用范围狭隘,则称之为‘狭义’,其有更广的适用范围者,则称之为‘广义’。如表达方式源于日常用语,则狭义者常与所谓的核心范围重叠,后者系依该用语之用法首先意指者;广义者则经常包含边缘范围,后者系依一般语言用法有时亦将意指者。假使逾越了――尽可能作广泛理解的――边缘范围的界限,则已非解释,同样地,如将无疑属于核心范围的现象排除于外,亦已非解释。”前引B22,第228―229页。
另一种观点以德国学者菲利普・黑克为代表,他形象地描述了“三区域模型”的模糊性概念,他指出:“概念的核心、距离最近的词义、概念的延伸使我们逐渐认识了陌生的词。它好比黑暗中被月亮晕围绕的月亮。”PH.Heck,Das Problem der Rechtsgewinnung(1912)-Gesetzesausleg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1914)-Begriffsbild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1932),in:Studien und Texte zur Theorie des Rechts,Bd.Ⅱ,hrsg.von J.Esser,redigiert von R.Dubischar,Berlin1968,S.66,156.转引自前引①,第82页。 德国有很多学者都赞成他的观点。魏德士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概念的核心领域,其含义归属于某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没有被明确限定的‘月晕’内,某个事物是否归属于某一概念(词)中还需要特别的检验,这种归属性充满疑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月晕’之外不会有其他事物包含于这个概念中。当月晕的两个边界(向内部与向外部)没有明确界定时,那么困难就更大了。”前引①,第82页。 可见,依据“三区域模型”的模糊性概念理论,任何一个刑法概念的语义空间都存在着所谓的“概念核心(肯定选项)”、“概念外围(中立选项)”以及“概念之外(消极选项)”前引⑨,第53页。 的区分。其中那些可清楚地被涵摄到概念下的对象或案例,也就是所谓的“肯定(积极)选项”,构成了概念的核心区域。与之相对,所谓“否定(消极)选项”,是指处于这个概念之外的,绝对不会被纳入这个概念之内的情形。概念外围则是由“中立(中性)选项”所构成。所谓“中立选项”,是指按照相关的通常的概念界定,或者根据社会生活中通常的语言使用习惯,均无法明确是否应该被涵摄在这一概念下的情形。此时,就需要由法官或法学家进行决定。因此,在解释刑法时针对肯定选项与否定选项不会产生问题,容易引起问题的是中间选项,具有模糊性的法律概念都属于这一范围。
综上所述,对于模糊性概念,不论是“两区域模型”的“阴影区间”,还是“三区域模型”的“中间选项”,法官必须通过目的论解释方法对它们作出解释,从而使该模糊性概念的语意变得清晰而明确。 (二)多义性概念
所谓多义性概念,主要是指“不同的人赋予同一语词的观念内容,可能或多或少彼此不同”。前引B34,第31页。 多义性概念之所以存在,从语言哲学角度而言,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是最佳解释:“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型、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据此,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词与其指涉对象之间既然是一种“家族相似性”的关系,那么语词必然带有多义性。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多义性概念则是一种解释的框架,在该框架之内其表达的意义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一方面是因为语词作为其所提示的,旨在通过人们的联想唤起特定意识内容的符号。使用某个语词的人,其所赋予该语词的意识内容,总是与其对话者的对象对该语词意涵的理解存在一些分歧;不仅如此,甚至某个社会群体中的多数成员,对同一个语词的意涵也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认识。据此,语词自然具有“多义的”属性。而且,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看,法律概念的含义随着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迁,从而直接地影响语词的含义,并进而间接影响法律概念的意义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在法律概念形成之初到其适用之时的观念变迁,亦可使某种单义性的法律概念向多义性概念转变。甚至有学者认为:“单义性法律语言的理想是不能去达到的,它也不值得去追求,因为法律语言,也必须是一种活生生的、两个面向化的语言。否则,它将无法有一个向日常语言,市民的语言的延续线。”[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由此可见,法律概念的多义性很难克服,正是通过这种多义性概念,立法者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其有权在多种意义中决定规范应具有的意义。所以,法律条文仿佛橡胶所制,具有无限的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明确指出:“是故,如果不诚心努力,取向于公义,探求法律的规范内容,强词夺理出诸学者专家或甚至公务员与公务文书,皆有可能。防止之道,在于发展有纪律的方法,使私欲之不理性的驱使能够受到控制,不到处横流,无所忌惮。”前引B25黄茂荣书,第301页。
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多义性概念的存在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可能基于概念语词的多义性。例如,‘物’可能是一个‘物质的’对象(作为财产权、盗窃、贪污、毁损财物的对象),一个程序的对象(‘审理案件’),或也是(在错误异议中)的‘行为对象’。”[德]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考虑到语言作为人类交流沟通的基本工具,世界只有通过语言,而不能外在于语言存在。因而法律必须以语言为载体而存在,从法律确定性角度来看,具有单一性意义的没有歧义的法律概念是约束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最佳形式。但这只是一种法治的理想图景,距离现实遥不可及。因为作为以语词表达的法律概念,也只有通过语词的形式才能传达这些概念。因此,考夫曼指出:“单一性的及精确性的代价是,使语言僵化,并因此将它简化为一个小小数目的符号。(日常)语言的不单一性,保证了一种流动性,它的动态性,以及它能够涵盖的多面性。简单地说也就是它的活泼性,以及具有历史性。”前引B44,第177页。
既然法律中的多义性概念不可避免,其又容易导致不确定性,那么如何才能澄清多义性概念的意义?对此,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哲学的立场,将语词的意义与语词的使用及其目的联系起来:“在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的各种情况中有数量极大的一类――虽然不是全部,对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明它: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前引B43,第31页。 这一论断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从刑法角度,张明楷教授所谓“当刑法用语具有多义性时,解释者必须根据正义理念、上下条文的关系,来选择用语的确定含义”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2页。 正是这种思想的应用。但是,如果借鉴“家族相似性”理论来考察刑法的法益,会发现刑法具体规范所具有的规范目的,经由相似性的考察,可以整理为一个法益的抽象图景。据此,可以确定具有同质性的法益保护规范,而这就需要目的论解释来完成。因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朴生教授指出:“刑法之解释应本其目的论之活动,在法律使用之用语意义范围内,具体化其内容。裁判之任务,即在适用法律于各个具体案件,裁判官应本其目的论之法的解释活动,使法律之意义具体化,补足非一意性之法令的意义内容。”陈朴生:《罪刑法定与行政刑法之解释方法》,载《法令月刊》1986年第37卷第5期,第5页。
(三)规范性概念
所谓规范性概念,根据魏德士教授的观点,主要是指“法律规定常常还包含某些概念,要理解这些概念,必须先作出判断。这些包含价值标准的概念称为规范性概念”。前引①,第89页。 由此可见,规范性概念与价值判断密不可分,因而始终伴有释法者的价值评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德士教授认为,“只要概念包含了判断因素,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规范性概念”。前引①,第89页。 与此对应的应该是刑法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对此,德国学者麦茨格指出:“在法官确定构成要件要素时,依据法律对其所要求的认识、判断活动的性质,可以区分为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即当立法者以日常生活用语单纯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形成构成要件时,法官对此要素的行为构成事实的认识,仅需要进行感性的知觉认识的判断就能够确定的要素,即为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与之相对,当立法者并不是对相应客观事实的单纯进行描述,而是采取极其概括的描述,因而仅是提供了进行价值评价的空间,在适用法律时,法官必须要进行价值判断补充评价的要素,则是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Vgl.Mezger,Vom Sinn strafrechtlicher Tatbestande,Festschrift fur Trager,1926,S.214ff. 因此,在确定构成要件要素是否存在的问题上,无需添加价值评价,法官仅是借助感性的知觉认识即能够确定的要素就是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相反,法官必须经由其补充规范的、价值评价的判断,才能确定的构成要件要素,则是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即所谓规范性概念。例如,我国《刑法》第237条关于“猥亵”、“侮辱”等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如恩吉施所指出的:“此规范性概念经常是特别高度不确定,并因此产生许多制定法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同时还有非肯定和相对不受约束性的例子。”前引B46,第134―135页。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规定了规范性概念的法律条文时,单纯的文义解释方法很难获得确定的结论,这就意味着法官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进行价值评价,目的论解释于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对此,德国学者许i曼教授的分析更为深入,他认为:“以下透过例子来阐释这三项概念范畴:作为科予罪责的前提之可期待性概念仍然是纯粹规范性概念,它没办法让归属于这项概念的案件事实一开始就被认识到。作为进一步的科予罪责前提的个人可避免性,相对地本身是一个纯粹经验性的概念,也要按照其意义来确定,但在实务上却碰到明显适用上的问题,一开始是意志自由的问题,到后来则是在精神性或心灵性疾病诊断上的问题。最后的例子是直接行为决意的概念,依据刑法典第22条规定,它确定刑事可罚的行为着手的开始,它本身是一项经验性概念但同时也是一项非常不明确的概念,而进一步精确化这项概念只能藉由刑事政策―目的论式的方法才能做到。”[德]伯纳德・许i曼:《作为学术的刑法释义学》,载许玉秀、陈志辉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i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春风煦日论坛2006年版,第144―145页。 (四)概括性条款
所谓概括性条款,又称为一般条款,主要是指:“法律中常有某些内涵和外延不确定,具有开放性的指导性规定”。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由于其经常使用如价值概念等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概念,因此有些概括条款与前述的规范性概念容易混淆。但二者还是有差异的,我国学者郑永流教授指出其区别体现在:“前者是一个完整的基础法律规范,后者仅具有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特征。”前引B56,第241页。 刑法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本来应该尽力避免使用概括条款的规定,因为此类规定直接损害了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德国学者韦尔策尔教授曾深刻地指出:“威胁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个基本原理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类推,而是来自不确定的刑法!”Welzel,StrafR11, §5Ⅱ3.转引自前引B32克劳斯・罗克辛书,第100页。 因此,某些概括性条款由于背离了刑法明确性的最低要求是被禁止的。例如,恩吉施即指出:“一如慕尼黑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初所设计的一般条款那样:‘每种违反革命的原则的行为将被处以刑罚。这种刑罚处在法官的自由裁量之中。’这类可罚性规定的一般条款在法治国中被唾弃。它们与‘无法无罪’原则不可协调”。前引B46,第150―151页。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刑法中还允许存在概括性条款?对此,德国学者Naucke的分析很有道理,他指出:“一是通过概括性条款渗入刑法领域的国家权力有所增长;二是权力行使方式有所改变,现代法律规制对于灵活性、变动性与适应新政治法律目标的能力产生强烈需要;三是出于不可阻挡地追求个案正义,追求对有利或者不利于行为人或被害人的行为的细微情状的实质性评判的需要。”Naucke,uber Generalklauseln und Rechtsanwendung im Strafrecht,J.C.B.Mohr,1973,S14―15.转引自劳东燕:《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因此,概括性条款的真正意义在于,适应国家权力膨胀的立法技术的要求,通过概括性条款较大的普适性,使司法实践中大量的事实构成无漏洞并且有适应能力地满足一个构成要件,承受一个法律结果。
概括性条款具有两种属性:首先是鉴于其规范内容的不确定性,导致法官适用法律裁判案件已经不再经由逻辑上的涵摄方式,而是通过自由裁量的方式进行。其次是法律之外因素考量的特性,即在适用概括性条款时,对其进行评价涉及的多是与法律之外存在的道德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事实,并不涉及法律本身。因此,当法官面对概括性条款时,必须进行独立的价值评价,目的论解释于此不可或缺。
四、代结语:如何规避目的论解释功能的内在危险
目的论解释的基本功能是承载刑法的价值评价,而其功能界限即在于和可能的字义界限一起标定刑法解释的边界,厘清目的论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如何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怎样确定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界限,这是世界性难题”。刘明祥:《论刑法学中的类推解释》,载《法学家》2008年第2期。 更有学者感叹如何区分类推适用与扩张解释确是“刑法学永恒的课题”。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笔者认为,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不是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因为他们必须将法律规范的目的作为权威依据展开解释,脱离法律规范的目的解释是无法进行扩张与限缩的,究其实质,二者就是解释的结论而非解释的方法。在此,可以将二者视为目的论解释方法的具体载体或者体现,也就是说它们是目的论解释方法的下位概念,为了避免歧义可以称之为“目的论扩张解释”和“目的论限缩解释”。因而通说的命题“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可以转化为目的论解释的内部问题,即“目的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从而使目的论解释的界限也因之转化为刑法解释的界限。因此,所谓“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也就是目的论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别。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理论思考,参见王祖书:《描述与分析:刑法目的论解释及其周边概念关系的厘清》,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39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5―71页。 日本学者关哲夫对日本刑法理论关于目的论解释和禁止类推解释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梳理,将其概括为三种立场:“第一,坚持严格解释的要求的立场,被称为严格解释说。第二,与第一种立场相反,是基于目的论的解释以实质的解释为指向的立场,被称为实质解释说。第三,依据具体的解释情况,调整严格解释的要求与目的论的解释的立场,被称为调整解释说”。[日]关哲夫:《论禁止类推解释与刑法解释的界限》,王充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0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页。 可见日本刑法理论也是站在目的论解释与类推解释区别的立场上展开理论研究的。在我国,也有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明确指出:“适用目的解释时容易滑向类推解释”。前引B11,第83页。
鉴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意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此刑法解释必须坚持严格解释的立场,而必须反对任意解释。“刑法应该如何解释,解释应当遵循何种规则,是罪刑法定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法律是可以任意解释的,由于语言本身内涵的复杂性,边界的模糊性,就使法条的规定难以表明确定的原则,使罪刑法定的价值大大降低。因而,禁止任意解释,是使罪刑法定的价值得到实现的重要方面。”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因此,为了规避目的论解释滑向类推解释的危险,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大宪章机能,就必须以“可能的字义”设定刑法解释的范围,然后在该范围内采取目的论的解释。具体而言,当法官面对有待解释的刑法具体条文时,首先必须通过文义解释来确定该法条的“可能的字义”范围,在该范围之内由于没有脱离“可能的字义”界限,因此就是合法的解释。与之相对,超出该范围之外的则是另造新的法律规则,这已经不是解释。可见,语言本身具有提供方向、指引释法者向一定方向前进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出发点,是不够充分的。“法学解释不是对先前思考的再思考,而是将已经思考的东西思考完毕。它出自于对法律的语文学解释,是为了以后能够超越语文学解释――这就像一艘船在出航时是由领航员掌舵穿过港口水域,引至规定的航道上,然后再由船长引导在公海上寻找自己的航线。法学解释完成了从出于立法者精神的解释到规定的一种不可察觉的过渡,解释者将自己‘变成了立法者’。”前引B20,第115页。 同时,对于刑法条文中需要补充价值的不确定概念,诸如前述模糊性概念、多义性概念、规范性概念以及概括性条款等,存在刑法自由的法发现之解释空间,一般而言在此类情形下,才必须依据目的理论解释为之,也只能通过目的论解释才能获得刑法条文规定的真正含义。
Abstract:It is note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legal interpretations since it has an insepar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trend of free-law movement. It is rather important to define the function of the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for fear that it should be abused.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e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is to appraise the value of criminal law rather than to fill in the loophole of criminal law. As to some uncertain concepts in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in need of value supplement, such as fuzzy concepts, ambiguous concepts, normative concepts and general provisions, they can only acquire authentic meanings by means of the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ormative concepts general provisions